作者:蜜雪兒.庫瓦斯(Michelle Cuevas)
繪者:楊允城
責任編輯:吳愉萱
出版社:三采
獻給不完美的我們
和每個深愛我們的人
【活動】詳情請見 此
楊允城遇見《樺樹與鴿子》 圖+文創作展 (免費參觀)
展出時間:2013年3月1日~5月31日 Mon-Sun10:00-19:30
本部落格相關連結
獻給不完美的我們
和每個深愛我們的人
我叫鴿子.瓊斯,由會畫畫的印度大象扶養長大。爸爸和媽媽把我留在孤兒院的階梯上,再也沒有回來。於是我爬出提籃、一路爬過城鎮,最後在暴風雨的樹葉堆中被樺樹發現,從此住在這隻白色大象的背上。
很多人覺得住在大象的背上是怪事,但我跟樺樹在一起感覺很安全。「安全」就像愛,是種奇怪的東西,不見得會照著我們選擇的組合出現。
我十歲生日那天,樺樹問我有什麼願望,我說我們必須去到巴黎讓他成為藝術家。我們搭上火車,不小心被關進了紐約動物園,然後又在好萊塢變成名人;當我們終於來到夢想中的巴黎,卻出現了一個穿著青蛙裝的男人,他說他是我爸爸……
樺樹與鴿子帶著愛情和夢想出發,一路上充滿驚奇,永遠不知道接下來會遇見什麼人、發生什麼事;然而心碎、失望和離別,卻成就了他們旅途中最美麗的風景,美得讓人捨不得結束這趟旅程,捨不得結束這個故事。
作者簡介
蜜雪兒.庫瓦斯 Michelle Cuevas

關於自己的故事,庫瓦斯是這麼說的:
我在復活節的前一晚出生,在群山與湖泊的環繞之下長大,我的爸爸以前是流浪樂團的鼓手。我八歲的時候寫了第一本書,是一隻會說話的鞋,因為鞋子有舌頭。我也有騎過大象,獨自住在樹林裡的小木屋,在無風的日子搭乘熱氣球。我有一隻貓,可惜他有焦慮症。我會吹薩克斯風,我知道魚如何在空中飛。我喜歡恐龍,一定要列出長長一串我最喜歡的恐龍的名單。我最喜歡的書是《夏綠蒂的網》,作者E.B. White是我的英雄。如果你問我,為孩子寫故事有什麼好,我會告訴你,若是能讓年輕的讀者看見一個繁花盛開的世界,以及生活中常常被人忽略的美好魔法,對我來說將會是最快樂的事。
蜜雪兒.庫瓦斯求學時在威廉斯學院主修英文,隨後在維吉尼亞大學研究所取得創意寫作課程的藝術碩士學位。曾在紐約惠特尼美術館工作。目前住在美國麻州創作她的第二和第三本小說。
台灣版繪者簡介
楊允城
Illustrator for the Taiwanese version:
Clement Yang

image courtesy of Clement Yang's family
照片由允城媽媽提供
與長大了的鴿子年紀相同的十歲台北市國小學童。一歲起便在家裡的牆上滿滿塗鴉,對畫畫情有獨鍾。三歲時隨家人旅法國巴黎一年,流連於大大小小的博物館、美術館與藝廊之間,當然也包括衝擊鴿子與橡樹心靈的偉大羅浮宮,也許就在那時,美的種子已在他心底悄悄地播下。而後隨著時間,種子發芽破土,以自己的方式抽長舒展,畫畫自然而然成為他每日生活的一部分。他的筆觸無羈自在卻又理所當然,彷彿最單純的快樂,並不需要推論,更不需要理由。如同樺樹的話語:「最耀眼的藝術作品,能帶給人們最純粹的喜悅的那些,也許它們不需要被人碰觸或解釋,只需要用心來觀看。」
3、這麼單純的東西
我天生就是那種不安於室的人,好似風滾草,你也可以說我是漫遊者。爸媽把我留在孤兒院階梯上的那晚,我沒有傻傻等待別人發現,而是直接爬出提籃進入世界。
我一路爬過城鎮,最後在葉子堆裡安頓下來過夜,就在老舊洗車行的那棟樓房附近。午夜,暴風雨從森林的邊緣急馳而來,幾滴肥大的雨水轉眼變成簾子般的滂沱大雨,伴隨著橫向吹掃的狂風。男男、女女、孩童、貓咪與老鼠全都窩在室內,聽著雨水在錫製屋頂上咚咚作響。在這世界上,只要天一開始下雨,有的人會立刻關起窗戶,有的人則會跑到屋外。或許是命運的安排,我跟樺樹正好屬於第二類。
在離我不遠的地方站著一棵老樹,其中一根大樹枝上密密實實地長滿苔蘚、蘭花與渴望往高處生長的其他植物。雨水注滿了蜷起如喇叭的樹葉,也讓樹根四周的泥土吸飽水份。在地球上活了這麼多年後,這棵老樹終於不堪這般沉重負荷。一陣特別疾勁的強風劈來,一根樹枝斷裂、猛砸落地,接著整棵樹搖搖晃晃、吱嘎作響,最後一路倒向附近的矮樹叢,好似將紅海一舉分開。老樹倒躺於側,暴露了盤根錯節的部分樹根,另一部分浸泡在深黑色泥水裡。樹木倒落的地點距離我睡覺的地方僅僅一英尺。那聲轟然巨響把我吵醒。雖然我沒放聲大哭,但樺樹還是看到我了。
他緩緩湊近,往下探出長鼻,嗅嗅我的腦袋。大象的鼻頭感覺好像吸盤,把我逗得呵呵笑。他用長鼻把我抬起來,我倆四目相對。「我叫樺樹,」他說,「因為我一身白,就像樺樹,所以他們這樣叫我。」
「阿嘎,不拉普,各兒苟。」我回答。
「我想你需要一個名字,」樺樹說,「既然別人是用樹木幫我取名,你小不嚨咚的,也許可以用小鳥的種類來幫你命名。應該取個高尚、氣派的名字,也許用獵鷹或隼,鷸或翠鳥,雀鳥或──」
就在那時,一隻笨拙的鳥兒降落在我們附近的樹枝上。她胖嘟嘟又灰撲撲,身上缺了好幾根羽毛。我喜歡那隻鳥,於是鼓起掌來,咯咯發笑。
「鴿子?」樺樹說,「你想叫做『鴿子』?」
我再次拍拍手。
「可是鴿子很噁心,」樺樹說,「她們是鳥類世界的鼠輩,會吃垃圾,而且胖到飛不過五英尺的高度。」
「不好意思,」鴿子對樺樹說,「我們鴿子可不是都跟你一樣苗條。」鴿子停在她的樹枝上,在離開以前唱了幾首歌給我們聽。她唱得不大好,但我喜歡那聲音。也許是讓我想起了家的關係。
「小寶寶,那你就叫鴿子吧,」樺樹說,「你會需要一個姓,簡單的姓,像『瓊斯』那樣的姓。對了,就叫瓊斯吧。」朋友們,那就是我變成鴿子‧瓊斯的經過。
隔天早上,樺樹走近團長,用象鼻吹出喇叭般的響聲,然後把我高高舉起給團長看。
「寶寶的耳朵大得不得了,」團長譏諷,「要是馬戲團還在,我搞不好可以給他一份工作,表演大耳怪人秀。可是我現在只有這家洗車行,你要我……洗娃娃嗎?」
樺樹搖搖頭。他拿起洗車用的水桶,一把丟到門外,再舉起海綿,也把它扔了出去,好強調自己的立場。
團長一臉困惑。「辭職?你要辭職?你滿腦子白日夢,作夢中間的空檔都還來不及把車子沖乾淨。你是我認識過最平庸無才的大象,竟然還想辭職?我才炒你魷魚咧!」
即使我只是個寶寶,我也一點都不喜歡團長。我不喜歡他傲慢的語調,也不欣賞他翹捲的八字鬍,更不喜歡他慌慌張張從一處趕往另一處的模樣,好像螃蟹手忙腳亂橫越自己的影子。
樺樹失業之後做的第一件事,就是花點錢,到商店裡買了一只籃子。他把嬰兒毯、搖鈴玩具、一瓶牛奶放進籃子裡,把籃子抬到背上,然後用長鼻把我擱在裡頭。他現在看起來真的就像棵樺樹:白色樹皮上佈有黑色紋路,枝枒當中有個小窩巢。
我用一雙嬰兒大眼向四周張望,從樺樹背上望出去的風景只有無邊無盡的藍天。我看到頭頂上有個大鳥的形狀,有如當初掛在小床上的活動吊飾盤旋不停。牠滑翔越過太陽,我一時只能看見牠的輪廓。我發出嘰哩咕嚕聲,接著牠鼓動羽翼飛離,世界再次充滿可愛的陽光。我聽著樺樹的心跳好像沉穩的鼓聲,一聲一聲說著「Thankyou、Thankyou、Thankyou」,不久就把我哄得睡著了。
樺樹住在城鎮的邊緣,睡在勉強湊合著用的房子裡,說真的,那只是一片屋頂加上充作牆壁的三片木板。木板是從以前馬戲團的舊車廂拆下來的,上頭繪有動物。樺樹先把它們拆開之後再拼湊起來,於是動物的身體部位全部搞混了,獅子的腦袋長在犀牛身上,猴子的腳跟面露微笑的鱷魚相接。我跟樺樹就睡在那裡,我們對我們的家都相當滿意;要是沒有梯子,沒人碰得到我。
第一天晚上,我睡不著,在樺樹的背上翻來覆去。那陣騷動吵醒了他。他盡量放輕動作,把長鼻往後伸過腦袋、探進籃子,用鼻尖慢條斯理輕搔我的肚皮,離開,然後又湊過來搔了搔。我先是微笑,再來哈哈笑開,同時伸出自己那雙小手。
有人說,寶寶的雙手是世上最柔軟的東西。而大象的皮膚並不是。大象的皮膚就像赤腳男人的乾糙腳跟。當我把手貼在樺樹的長鼻子上時,他知道自己這輩子從沒體驗過那麼細緻的觸感。當他感受我那屬於新生兒的碰觸時,他說:「這種東西一直以來都到哪去了?我尋遍各處,就是想要感受這麼單純的東西。」
很多人以為住在大象的背上是怪事,但我跟樺樹在一起時覺得很安全,就像小小魚安全地寄居在鯊魚肚腹下。「安全」就像愛,是種奇怪的東西,不見得會照著我們選擇的組合出現。因為大象的天性會極力保護自己的嬰兒,所以樺樹一直不准我離開他的背。我是說,真的完全不行,從來都不可以。但我一點也不在意,我就在這睡覺、吃飯、玩耍,樺樹還會用長鼻吸水幫我淋浴。等我到了十歲的時候,甚至在樺樹的背上有了自己的轎屋,我可以在那存放幾件個人物品:牙刷、尿壺、梳子跟書本。大象的背部比較靠近太陽,溫暖的陽光沖淡了色彩,我的世界一派寧靜。
除了我之外,還有很多人都是動物養大的。
從前,每逢淡季,馬戲團就會到一個小鎮安頓下來,那個小鎮小到連名字都沒有。某一年的冬天,馬戲團永遠關閉了,大部分的成員說:「待在這裡就跟待在其他地方一樣好。」於是他們就留在這個小到無法命名的城鎮。很快地,這裡就變成沒那麼平常的人們所居住的平常地方。
有些前任的馬戲團成員在馬戲團關閉之後,輕輕鬆鬆就融入自己的新行業。吞火人法蘭茲變成受人敬重的消防隊長;巨人傑克轉職房屋油漆工,他說:「我連梯子都不需要呢。」四臂芬妮開始在當地的餐館負責翻煎漢堡肉,煎鏟動得飛快,停也停不下來;還有瘦子芬恩,他負責清理煙囪,總是俐落地咻嚕滑進煙囪裡頭。
既然沒機會好好認識爸爸媽媽,我乾脆自己編造他們的故事,然後對自己述說那些故事直到入睡。在反覆說過那麼多次之後,故事變得越來越逼真,就像描繪回憶的畫作,也像恣意修改色調與比例的藝術作品,我可以透過那些破碎的色彩看見他們的人生。媽媽跟爸爸以前也在四處巡迴的馬戲團裡工作。嗯,我猜他們就是那樣認識的。我想像媽媽就是蓄鬍女,如果我現在可以跟她聊天,她就會跟我說自己長出鬍子的故事。「我本來是個有錢人家的美麗女兒,」媽媽會說,「我父親想把我嫁給隔壁的商人,可是我不愛他,時時祈禱自己可以躲過這樣的命運。婚禮前一天,我竟然長出鬍子,立刻澆熄了我未來丈夫的熱情。」
就在那時她認識了爸爸。我敢打賭,他第一次看到她的時候,一定覺得她很可愛動人。如果我現在可以跟他談天,他應該會說:「如果其他人都覺得某樣東西很醜,你卻覺得很漂亮,那肯定是真愛的徵兆。」
我想像在馬戲團裡,爸爸身穿青蛙裝,是眾所皆知的吞蛙人。他的秘訣在於對腸胃道系統近乎完美的控制力:先灌下大量的水,然後吞下活青蛙、蠑螈,甚至是小蛇。幾分鐘過去,他把牠們全吐出來的時候,牠們都還活蹦亂跳、扭來扭去的。媽媽可能愛上了他對待事物的善良──裡外都是;她知道如果他在胃裡那麼溫柔,那麼內心肯定柔情似水。
於是我想通了:爸媽之所以會拋下襁褓中的我,是為了隨某個馬戲團遠走高飛,重新推出吞蛙人與蓄鬍女的戲碼。有時候我夢到他們回來找我,我也跟著加入馬戲團。我會站在樺樹的背上,在表演場地的中央快跑繞場。眾人會歡呼吶喊:「看看那個小男生!好勇敢啊!」在我的另一個夢裡,我聽到媽媽在隔壁房間輕聲哭泣。可是當我醒來的時候,只聽得到樺樹的呼吸聲。你能夠想像嗎?如此深深思念某個人,思念到願意付出一切只為了再次聽到她的哭聲。
希伯來文版本 書封
5、大象畫家
「你聽,」某天晚上,天空佈滿厚厚的藍黑色陰影,我對樺樹說,「所有動物的聲音你都聽得到嗎?」蟋蟀、青蛙與樹蟬頻頻發出聲響。那種歌曲帶有某種韻律,而韻律來自每種生物等待放聲高歌之前的停頓。「我也聽得到停頓裡的聲音喔。」
「像是什麼呢?」樺樹問。
「嗯,比方說月亮。」
「你聽得到月亮的聲音?唔,你的耳朵還真特別!」
「其實是對話啦,」我回答,「月亮說,他厭倦自己在文學界的工作,厭倦自己老是出現在故事裡,厭倦自己身上塞滿乳酪、吸引狼人靠近。不過我又問他:『如果我們不需要你了,你怎麼辦?要是我們跟你說,我們有檯燈跟照明設備就夠了呢?』月亮承認,到時他會想念自己曾經有過的職業生涯。」
我們端坐在一片靜謐裡。蚊子叮咬我的皮膚,提醒我世界在哪裡結束,而我又是從哪裡開始。「你知道我還問了月亮什麼嗎?」我對樺樹說,「我問他,當他高高掛在天空的時候,可不可以順便找找我的家人。如果他們還活著的話。」
「嗯,這個請求滿合理的。」樺樹回答。
「你想,媽媽跟爸爸還記得我嗎?」我問。
「我知道他們還記得,」樺樹說,「我知道,因為我也曾經愛過然後失去過某個人。」他繼續說,「愛就像雨水,我記得它落在背上的感覺。水從我身上濺彈開來,好像鞭炮爆出的火光。我感覺得到每滴雨水,我感覺得到它們曾經屬於的海洋,感覺得到它們飛離的雲朵,也感覺得到它們往後的旅程──在花瓣上、蜜蜂翅膀上或是深入土壤裡的歷險。在雨中,我感覺自己完美無瑕,我感覺到心中的狂野,天空好似灰藍色的絲綢披罩在我身上,我根本不想躲開那陣雨。」
我的心痛了起來。當然了,我不用對樺樹說,他就知道我在想什麼。經過這麼多年的相伴,我的眼睛就是樺樹的眼睛,他的眼睛也是我的。長鼻與人鼻可以互換,我們吞吐著同樣的氣息;甚至連動作都有了默契,先是在心裡想著,然後行動,就像鵝群同時轉向一樣搭配無間。所以,即使沒有說出口,樺樹永遠知道我什麼時候心情不好。他會把長鼻伸過自己的腦袋上方,圍繞著我,直到我進入夢鄉。
當我睡著後,樺樹會靜靜拿出從二手商店買來的美術用品組。他擺出畫架,按照彩虹的順序,排出一管管的油彩:紅、橙、黃、綠、藍、靛青、紫。他會在調色盤上擠出一點藍色,再用長鼻抓起畫筆,用深沉的色彩沾滿柔軟的筆尖。他會吸一口氣,輕聲地說:「這是我最愛的部分。」然後在純白的畫布塗上第一筆。
既然樺樹是動物,動物屬於大自然,樺樹自然依照著大自然創造藝術的方式,來創造自己的藝術。大自然的藝術是蜘蛛網;是先用細枝精確搭疊、再用一綹女孩的如絲秀髮綁牢的鳥巢;是迷醉於光線而頻頻輕撞紗門的飛蛾;是彷彿用砂糖轉編出來的棉花糖般、精巧細緻的蠶蛹。大自然是一整群閃游的銀魚;是被秋意染得緋紅的樹葉,將湖水倒映成了紅色;是遼闊的草原與藍天,和一群野牛在地平線上創造出一道道色彩。
那晚,樺樹用盡調色盤上的所有色彩,畫出夏末的夜景。他畫出一片橙色天際,將一桶桶的光線傾倒於田野上,一路延伸回森林的黝黑邊緣。他畫出一條倒映天色的河流,悄無聲息、總是朝著海洋移動,流向我們可以重新找回失落已久的愛的地方。他在河畔的樹林裡畫了隻隻鳥兒,想像牠們對著河流訴說、朝著青草啼唱。樺樹想像,如果這首歌真正美麗,泥土、山巒與樹葉,萬事萬物自然都會隨著那些鳥兒一同歡唱;而那些無法高歌的事物的夢想,將會在放聲高歌的事物中被聽見。
有聲書評
凱宇專訪三采文化編輯部吳愉萱小姐
作者Michelle Cuevas 與大象
譯者留言 (2013.4.11):
朋友chiayu chang 讀完這本小書
來信說「簡單的故事卻有豐富的感情」
還送上了以下這張他自己畫的
可愛又溫柔的圖
最後,分享一首好歌
Ane Brun 〈Lifeline〉
lyrics source
All this time
I've been drawing your lifeline
As I held your hand in mine
I've been smoothing out your troubles
While my own I left behind
All this time
I've been painting our portrait
But I can't seem to make it shine
The angle doesn't seem to matter
Perhaps the problem's with the light
It's taking so long
And it's gonna take a little more
Please prove me wrong
Is it gonna take a little more
Ooh, in time
I will whisper speaks of gladness
Sweet release and the smiles
I'll be carrying your laughter
Like a favorite work of art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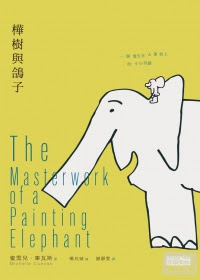









No comments:
Post a Comment